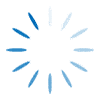这一夜,思及明儿要做的事情,谢逢舟总是辗转反侧,难以成眠。思绪如藤蔓一般缠绕,心头的波澜久久不能平息。
天色刚刚破晓,院中还留着夜雨的余凉,琅轩便快步进来,神色中带着几分不安与慌张。他在门外轻声禀报:“爷,宫里头来人宣旨,请您赶紧过去。”
谢逢舟尚在迷蒙中,听得此言,连忙披衣而起,步出卧房。
大堂之中,几位内监恭谨而立,鸿胪寺丞也在一旁候着。屋内气氛肃穆,却带着一丝难掩的喜气。
谢逢舟拱手行礼,低声道:“不知诸位大人莅临,有何见教?”
来者皆笑容满面,语气里溢出掩饰不住的祝贺之意。内监连连拱手,道:“谢大人,恭喜,恭喜!”
谢逢舟一时摸不着头脑,只得跟着笑了笑,恭敬询问:“不知有何喜事?”
领头的内常侍微微一笑,清了清嗓子,正色道:“谢大人还是先听旨吧。”
谢逢舟心中愈发疑惑,仍是依礼跪下。
鸿胪寺丞展卷高声宣读:
诏曰:
朕膺昊天之眷命,承宗庙之重光。大理寺司直谢逢舟,器蕴珪璋,行标竹柏。理宪清风,丹忱可鉴。孤贞克守,允协朕怀。
琅琊公主,毓德璇闱,柔嘉成性。年及笄珈,宜缔良缘。今命尚主,其制如左:
一、授驸马都尉,赐紫金鱼袋、银章龟钮,佩剑入朝。
二、赐永安坊甲第,工部营缮,依公主府规制。
三、纳征诸礼由少府监代行,赐绢三千匹。
四、宗正卿摄醮戒,太常寺备合卺仪。
五、追赠谢氏三代光禄大夫、郡夫人。
布告中外,奉敕施行!
福盛五年五月初九
院落内诏音回荡,字字如雷,落地有声。谢逢舟却只觉耳畔轰鸣,心口如被重锤击中。“尚主”二字,似一道天雷劈下,将他所有的期望、筹谋与温存心事劈得粉碎。
堂上众人满面春风,语气诚恳:“谢大人,这可是无上的荣耀啊,恭喜大人,贺喜大人!”
他却仿佛置身梦中,脸上没有丝毫喜色,只是怔怔跪着,指尖微微发颤。
琅轩在一旁看得分明,赶紧俯身,在他手臂上轻轻一按,低声劝道:“爷,这可是圣旨,您且先接下,咱们再从长计议。”
鸿胪寺丞与内监对视一眼,见状只当他是喜极而呆,便陪着笑脸催促:“谢大人,莫不是高兴傻了?快快接旨——圣恩浩荡,可不能怠慢。”
晨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落在檀香案几,屋内气氛肃杀而盛大。谢逢舟终于回过神,颤声谢恩,接过圣旨。心头却是一团乱麻:昨日还在筹谋提亲,今日却被天命强行改写前路。身负荣光,举世艳羡,可他心里,却只觉得彻骨的空寂与无助。
自古“荣宠”二字,多少人梦寐以求。可落在他身上,却仿佛裹着寒霜的锦衣,外表光鲜,内里却是一道道看不见的桎梏。
人生无常,不过如此,那日街市上的偶然一见竟生出这般波澜。
公主尊贵,尚主为荣,可他心底那一点私情、心事,却被这道圣旨无情碾碎,连挣扎的余地都未曾给他留下。
蕙宁正与绛珠一同在卧房拣拣草药,窗台上摆着新晒的黄芪,当窗日色淡淡。檀云自外进来,脚步轻缓,神色却似有千钧。她站在门口,肩头微微发颤,半晌才低声道:“姑娘……”
蕙宁偏头,唇角含笑,声音温和得仿佛春日细雨,打趣着:“怎么了?是不是犯了什么错,怕外公罚你?跟我说说看,无妨的。”
檀云却再也忍不住,眼圈一红,泪珠滚落下来,声音哽咽:“大老爷,还有谢大人……都在书房等着姑娘,说是、让您过去一趟……”
这般异样,蕙宁心头忽地一紧,袖下的手指不自觉攥紧了帕子。她不再多问,起身快步往西廊书房去。
廊下风过,竹影婆娑,天光却仿佛一下子暗沉下来。
书房中,吴祖卿倚在太师椅上,眉头紧锁。案几上茶烟袅袅,却无人理会。
谢逢舟立在窗前,背影挺拔,却带着难掩的颓唐。他听见脚步声,猛然回身,见到蕙宁,眼底陡然生出决绝的光。顾不得吴祖卿在场,他疾步迎上前,猩红着眼睛,握住她的手,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急切与颤抖:“蕙宁,你愿不愿意跟我走?”
“走?去哪儿?”蕙宁被他突然的举动惊住,却还是极力保持镇定,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
吴祖卿叹息一声,欲言又止,终究只是摇头:“济川,你冷静点……”
谢逢舟像是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痛苦与愤怒,声音几近嘶哑:“我冷静不了!我不要什么公主,我只要你!”
一句话如惊雷落地,蕙宁的脸色瞬间苍白,指尖微微发冷,脑海中也顿时了悟。她怔怔地望着他,泪意在眼眶里打转,声音轻得如风中残烛:“琅琊公主选的驸马……是你?”
谢逢舟避开她的目光,面色痛苦,嘴唇微微颤抖,却始终说不出否认的话。
蕙宁只觉心口被什么狠狠攥住,连呼吸都带着隐隐作痛。皇帝旨意如山,谢逢舟被选为驸马,这世间便再无转圜余地。若有,也只是让她屈辱为妾,委身于人檐下。
她怎肯?
若如此,三人俱伤,何必将苦涩延续?
她深深吸一口气,努力将眼泪逼回去,却仍有泪从睫毛滑落,抽出自己的手,强忍住颤抖,挤出一个清婉的笑意,声音温柔却带着决绝:“那真是恭喜你了,谢大人。小女祝你与公主百年好合,永结同心。”
谢逢舟闻言,心头一阵剧痛,几乎不能自持。他急急道:“蕙宁,你明明知道,我心里的人只有你。我不懂为什么忽然要让我做驸马,什么公主、郡主,我都不在乎!没有情爱的婚姻,于我而言毫无意义——”他暴躁地推开门,日光明媚,却似被乌云遮蔽。他的声音带着几分破碎和绝望:“我现在就进宫,我要去当着皇帝皇后的面说,我不爱公主,也不求荣华富贵,大不了不要这个官,也不要这条命……”
“可我想让你活下来,我想看到你幸福。”蕙宁轻轻地打断了他,声音柔和,目光里却带着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光芒。她的眼神依依不舍,仿佛要将他一生一世都刻进心底,却又分明是决然的认真,似玉兰花开,寂静而不可动摇。
谢逢舟闻言,身子一僵,原本聚在眼底的哀怨与愤怒,忽然被这句话揉碎成了无边的茫然。他张了张嘴,终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屋里静得连外头的风声都听得分明,吴祖卿在背后叹息着:“济川,你我都心知肚明,事情已经至此。你若执意如此,伤害的又岂止是你自己,或者公主一人呢?”言下之意,若是谢逢舟继续抗旨,吴家也难逃牵连。家国律令森严,皇权之下,个人的悲喜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谢逢舟缓缓垂下头,方才的急躁与愤慨,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无力与绝望。他的手指在袖中发抖,像极了风雨中孤苦无依的浮萍,只能随波逐流。
蕙宁强忍着心底的悲伤,俯身退后一步,郑重其事地行了一礼,声音温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温柔:“琅琊公主秀外慧中,绝色倾城,小女相信,这必定是属于驸马与公主的美满姻缘。”话已至此,谢逢舟那般聪慧的人,又怎会不明白蕙宁的深意?她已经用尽全部的温柔与坚强,把最后的体面和祝福都给了他,也给了自己一条从容退场的路。他只觉得唇齿间一阵苦涩,千言万语拥上心头,却只化作一声低低的叹息。
临别时,蕙宁将亲手抄录的《流芳阁小记》递到谢逢舟手中,从前总是觉得自己写的每一页都不完美,却又想着未来有那么多曼妙时光可以继续从容书写,如今才发觉,一切都是枉然。
扉页上字迹清秀,盈盈似兰,谢逢舟捧在手里,指腹轻轻拂过纸页,仿佛能感受到她温热的余温。
《流芳阁小记》讲的是前朝才女谢蘅与所爱之人有缘无分,天各一方。蕙宁最喜欢的,便是末尾那一段:“杜郎携余赴京,适逢陈家画舫泊于潞河。隔舟见崔氏抱婴嬉于舱前,彼正负手观灯,焰火明灭间,鬓角已染秋霜……流芳阁阶前青砖仍在,当年竹枝所书‘死生契阔’四字,今唯见苔痕深浅,雨渍如泪。”
她掩面拭泪,泪水冰凉,滑过指尖,心头一片空寂,不禁自嘲:原来世间最难的不是诀别,而是明知无望还要微笑着祝福。也许,从一开始她和谢逢舟便注定有缘无分。罢了罢了,这段情意,就让它如画舫隔水、流芳阁前青砖,长留心间,成为最美好的回忆吧。
她垂下眼睫,嘴角勉强弯出一抹浅浅的笑意。心中却在默念:有多少人,这一生都未曾拥有过这样纯粹的喜欢?她有,她已经很幸运了。等到将来,嫁与他人,白发苍苍时,还可以回忆起这段旧时光,回忆起年少时为一个人心动、为一场无疾而终的缘分流过泪的自己。
她望向窗外,海棠花不知何时已谢了大半。枝头残红点点,落英缤纷,一如她此刻的心境,空茫无依。
风吹过庭院,带着淡淡的花香和一丝寒意,吹乱了她的发鬓,也模糊了旧日的温柔。
聚散苦匆匆,此恨无穷。今年花胜去年红。可惜明年花更好,知与谁同?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