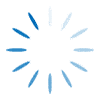俞琬缩在靠窗的皮沙发里,捧着一杯热可可,小口小口喝着。她换下了滑雪服,穿着奶白色羊绒毛衣,领口有点大,露出一小截白皙的锁骨,脸颊被暖气哄得红扑扑的。
克莱恩走向柜台去取那份黑森林。他当然注意到了,下午经过时,她那双黑眼睛是如何粘在那些洒满糖霜的点心上的。
像只馋嘴的小松鼠。
他站在那儿,即使穿着休闲的驼色毛衣,依然脊背挺直,与周围那些斜靠着大声谈笑的滑雪客截然不同,引得几位女士频频侧目。
就在这时,一个略带惊讶的声音响起来。
“赫尔曼,我的老天,真是你!”
两个男人裹挟着一身寒气走了进来,领头的是个棕发的高个子,笑容爽朗得像山间的风。
克莱恩转过身,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快的…无奈?
“埃里希,”他微微颔首,平淡地打了声招呼,目光又扫过跟在后面的男人,“威廉。”
“上帝作证,我们还以为眼花了!”名叫埃里希的男人大笑着上前,用力拍了拍克莱恩的肩膀,“是谁当年宣称,滑雪是‘浪费时间且充满无意义风险的娱乐’?嗯?冯克莱恩少爷?”
他的目光自然而然越过克莱恩,落在了窗边那个娇小的东方身影上。
女孩正低头,唇瓣微微嘟起,试图吹开热可可表面那层绵密的奶油,似是感觉到视线,茫然地抬起头来。
两个男人的表情立刻变得微妙起来。
“哦——嚯!”埃里希拖长了语调,笑容促狭,用手肘碰了碰身边的威廉,“原来‘风险运动’的定义,显然取决于陪伴对象?”
克莱恩的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。
“她是暂住我家的客人。“他打断他,声音冷了一度,“我对她的假期安全有监护责任。”
监护责任,多么正当又蹩脚的理由。
对方显然不信。埃里希挑眉,笑容越发灿烂了,“‘负责安全’需要带来楚格峰?赫尔曼,你什么时候这么有爱心了?”
克莱恩的耳根红了——这次很明显。
埃里希凑近些,压低声音:“说真的,很漂亮。哪里认识的?”
“够了。”金发男人的声音骤然冷了一度,转身朝女孩走去,用行动表示话题结束。
但埃里希显然不打算放过他,竟三步并作两步,自来熟地坐到了俞琬对面。“小小姐,自我介绍一下,埃里希·冯·施泰因,我们是克莱恩在柏林军事学院时的同期。”他朝俞琬眨了眨眼,“所以,你有权知道真相,关于这位监护人的一些……有趣往事。”
女孩不知所措地看向克莱恩,又看看面前这个过分热情的男人,无意识握紧了杯壁。
“埃里希。”克莱恩警告道,将蛋糕放在俞琬面前,自己也坐下来,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保护姿态。
“放心,都是好话!”埃里希举起双手,故作无辜,“小小姐,你知道这位先生当年外号是什么吗?”
俞琬摇了摇头,好奇心却被勾了起来。
“北境的冰封王座!”埃里希戏剧性地压低声音,却又确保周围几桌都能听见,“不是说他来自北边,是说他的心,硬得像格陵兰的冰盖。那时候,多少柏林名媛,排着队想融化这座冰山,情书送到宿舍,你猜我们克莱恩少爷怎么处理?”
金发男人的太阳穴突地跳了一下。
威廉接过话头,模仿着当时男人毫无波澜的语气:“无暇处理无关物品,然后扔进了碎纸机。”
这话一出,周围几桌响起低低的哄笑声。
女孩偷偷看向克莱恩,他板着脸,嘴唇抿成一条直线,整个人像一座要喷发的火山似的。
原来他以前这么……不解风情吗?女孩在心里勾勒着那个严肃的军校生形象,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。
“所以,”埃里希总结,“现在这位‘冰封王座’先生,不仅亲自教人滑雪,还——”他指了指男人下意识放在靠背上,近乎圈住女孩的手臂,“防护得这么周全,真是令人感动的监护责任!”
克莱恩终于放下了手,但也向前倾了倾身,宽阔的肩膀将女孩完全挡在身后,湖蓝眼睛寒意沉沉。
“说完了?”
声音不高,却让木屋里的温度骤降。
埃里希再次举起双手做投降状:“好好好,不说不说,不过既然遇到了,一起吃晚饭?山下那家鹿肉餐厅,我请客。”
“不用。”克莱恩干脆打断他,转身向女孩,“我们换个地方。”
“别这么冷淡。”威廉插话,“难得在雪山遇见,小姐,您想尝尝正宗的巴伐利亚鹿肉吗?配黑啤酒和土豆丸子,赫尔曼以前能吃三人份。”
他们显然把俞琬当成了突破口。
女孩怯生生地看向克莱恩。她其实……有点好奇。想看看克莱恩军校时的样子,想听那些她不知道的故事。
这么想着,便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角。
克莱恩低头,对上她的目光。那双黑眼睛里盛着未散的窘迫,但深处,确有一簇期待的火苗,被他敏锐捕捉到了。
她想留下?想听这些家伙继续编排我的“事迹”?
这让他耳根的热度不降反升,心里还泛起一丝无奈的躁。
可最终,他妥协了。
“一小时。”他咬着牙说,“之后我们要回去休息。”
“成交!”埃里希抚掌大笑,又重重拍了拍克莱恩肩膀,力道大得能让寻常人踉跄。“晚上七点,麋鹿印记餐厅,不见不散。”
两个老朋友心满意足地离开,餐厅重新恢复了之前的嗡嗡声。
克莱恩这才在她对面坐下。
“……给您添麻烦了。”俞琬小声说,用银叉无意识戳着黑森林上的樱桃,果汁渗出来,在奶油上晕开一小片绯色。
“不麻烦。”男人端起咖啡,热气稍稍模糊了过于冷冽的眉眼,“只是两个话多的朋友,如果你不想去,我们可以不去。”
“我想去。”女孩连忙说,声音小了下去,“……想尝尝鹿肉。”说完,觉得自己表现得太贪吃,又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去。
克莱恩看着她微红的耳尖,嘴角牵了牵。
“那家的鹿肉确实不错。”他说,“不过黑啤酒,你只能尝一口。”
语气俨然一个严格的大家长。
俞琬点点头,挖了一勺蛋糕。巧克力甜香和樱桃的微酸在舌尖融合,让她满足眯起了眼睛。
克莱恩看着她小猫似的表情,指尖在咖啡杯上敲了敲。
带她来是对的,他想,尽管有意外干扰。
但她开心,这个认知清晰而坚定。
麋鹿印记餐厅,七点半
包厢的墙壁上挂着巨型鹿角标本,壁炉里的火也比大厅更旺些。
“克莱恩的滑雪技术,当年在我们中间可是这个。”埃里希喝了一大口黑啤酒,翘起个大拇指,“还记得那次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雪训吗?他敢跟教官打赌,从那条黑道倒滑下来,赢了三条高级香烟,我们分了半个月!”
克莱恩坐在女孩旁边,面无表情地切着盘子里的烤鹿肉。“夸大其词。”
晚餐比预想的愉快。
鹿肉鲜嫩,土豆丸子绵软,连俞琬被允许尝的那一小口黑啤酒,都有种奇妙的麦芽香气。埃里希和威廉虽然爱开玩笑,但都刻意避开了任何与时局相关的沉重话题。
她听得眼睛发亮,时不时偷偷看着克莱恩。
而他大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用餐,只在某些夸张的桥段冷冷插一句:“假的。”或者“他记错了。”
他特意让女孩坐在靠墙的内侧,这样她只需要面对他一个人,不用承受其他目光。
但防护效果很快被证明有限。
“所以,”埃里希给俞琬倒了杯热苹果汁,笑容像只狡猾的猞狸,“小小姐是怎么俘获我们这位冰山的?”
女孩差点呛到,捂着嘴咳嗽起来,白皙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。
克莱恩递过手帕,凉凉扫了埃里希一眼:“适可而止,她不需要回答这种无聊问题。”
“无聊?”威廉温和地笑着,摇了摇头,满是感慨。“赫尔曼,想想看,当年连莉莉亚娜·冯·俾斯麦小姐那样的追求者你都……唉。”他适时地住了口。
“莉莉亚娜?”俞琬小声重复,悄悄捏紧了亚麻餐巾。
克莱恩的眉头拧得更紧了:“那只是谣言。”
“谣言?”埃里希夸张地挑眉,“人家可是在毕业舞会上当众说‘非克莱恩先生不嫁’!结果你第二天就申请调去了东普鲁士实习,把人家姑娘伤心得一年没参加社交季。”
话音刚落,女孩放下了刀叉,睫毛颤了颤。
克莱恩当然看见了,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收紧。她在意这个?
他声音里的温度降至冰点:“如果你们只想说这些,我们可以走了。”
“别别别!”埃里希连忙按住他,“好好好,不说别人,说说你!小小姐,你知道这家伙在学院多可怕吗?”
他转向俞琬,开始掰手指数起来。
“第一,每天六点起床,雷打不动,下雨下雪都一样
第二,所有科目全优,射击从来都是满分,枪械拆装速度纪录保持者
第三,格斗课把教官摔骨折过,当然那是意外。
第四……”
听到这里,女孩忍不住轻轻笑出声来。
金发男人的耳根此刻已经红透了:“……没有第四。”他端起酒杯猛灌了一口,喉结剧烈滚动着。
“有。”红头发的威廉举手作证,“第四,说梦话都在指挥作战,有一次演习,我们同帐篷,半夜听见他下令,第三梯队,向左翼迂回包抄!”
此时,连一旁的侍者都忍不住别过脸去。
俞琬死死咬着下唇,才堪堪没让笑声溢出来,可眼睛已然弯起来,她悄悄看向克莱恩,他此刻正用一种肃杀的神情切香肠,刀刀用力,像在肢解什么敌人似的。
他好可爱,虽然用“可爱”形容凶巴巴的克莱恩先生很奇怪……但他就是很可爱。
这个念头让她心跳没来由乱起来。
笑声稍歇时,埃里希忽然认真了几分。
“说真的,小小姐。这家伙虽然是个冰块,但……”他看向克莱恩,眼神里多了几分真挚的钦佩,“他是我们那届最值得把后背托付的人。”
金发男人切香肠的动作停了。
“所以,”埃里希举起啤酒杯,挤挤眼,那点戏谑又回来了:“这家伙的心是花岗岩做的,硬得很,但如果谁把那块石头捂热了,那大概就是一辈子的事了。”
空气陡然安静了一瞬,远处山风掠过松林的呜咽都变得异常清晰。
俞琬低着头,盯着杯子里的苹果汁泡沫,心脏砰砰砰跳着,声音大得生怕别人能听见。
克莱恩放下刀叉,金属与瓷盘碰撞出叮一声轻响。
“埃里希,”他的声音平静,“你喝多了。”
“我才没。”埃里希说到一半,对上金发男人的眼神,突然识趣地闭上了嘴。那眼神他太熟悉了——当年在模拟战壕里,克莱恩决定独自返回寻找失踪战友时,就是这个眼神。
平静,坚定,不容置疑。
“我们该走了。”克莱恩站起身,对女孩伸出手,“明天要早起。”
女孩下意识把手放进他掌心去,任由他把自己拉起来,向后面两人匆匆点了点头道别。
走出来时,凛冽瞬时间包裹了他们,两人沉默地走在通往木屋的小径上,鞋子踩在新雪上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走了不知多久,直到身后喧嚣已被松林吞噬,男人忽然停下了脚步。
他转过身,眼睛深邃得像冰川下的湖泊,直直看向她。
“刚才那些话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俞琬抢先开口,声音很小,不自觉绞着围巾的流苏。“是玩笑……我不会当真的……”
她垂下眼,不敢看他。
男人沉默了很久,山风掠过树梢,卷起雪粉,在两人之间盘旋飞舞,像一道朦胧的纱幕似的。
“那个莉莉亚娜,”他忽然开口,声音低沉,“我只在家族宴会上见三次。”他顿了顿,“埃里希夸大其词是他的毛病。”
俞琬愣愣看着他。他在…解释,和她解释?
“至于碎纸机的事,”克莱恩不自在地移开目光,投向银蓝色的雪峰,“……是真的。”
“诶?”
真实原因,那时我眼里都是战术和军衔,觉得感情是弱点。现在我知道我错了,他在心里说。
他重新看向她,目光专注得灼人:“所以,不要听信那些夸张的故事。”
俞琬仰着头,月光洒在她微微张开的唇瓣上。她就这样一瞬不瞬地望着他,望着他眼中那份近乎笨拙的认真。
忽然间,她隐隐约约明白了,他不是以监护人的身份在解释给被监护人听。
回木屋的路有些长。
俞琬跟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,小心踩着他在雪地上留下的靴印,仿佛在进行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游戏。
她的心口像揣着一只不安分的小鸟,餐厅里那些话语还在回响,搅得她心里乱糟糟的,有紧张,有羞赧,还有一点点……像融化的热可可般的甜。
路过一片平整的雪坡时,女孩停下来。
“克莱恩先生……”她小声唤他。
男人闻声回头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